
郑念原名姚念媛,1915年生于北京,长在天津。
祖父姚晋圻,清末民初大儒,
逝世后,时任总统黎元洪明令国史馆为之立传。
父亲姚秋武留日归来,军中少壮,官至将军。
家世显赫,加之本就天生丽质,
也就不难理解,郑念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,
就曾四次登上《北洋画报》的封面。
成为天津卫的风云人物。
要知道,上一个因登上《北洋画报》而名声大噪的人,是赵一荻,
也就是那个16岁与张学良私奔,
成就一段世纪爱情传奇的赵四小姐。
一时间,郑念成为天津名媛圈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,
凭己家世及美貌,
觅得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,
郑念本可书写出一段属于自己的爱情传奇。
这本也是那时天津名利场司空见惯之事——
不管家世如何,才情如何,
女以夫贵,这是当时女性都逃不了的命运。
未料,郑念的美,只是在天津昙花一现,
并无激起任何波澜。
郑念一步一个脚印,中学读完之后,
考入燕京大学,再远赴英伦,
获取世界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学位。
“明明可以靠颜值,偏偏靠才华”,
用来形容郑念,再恰当不过。
在伦敦期间,她与同校的郑康琪博士相识相爱,
并结下百年之好。
那年,她正青春,20岁。
在少女时代,她的美惊艳四方。
跨入青春时,她走进一段平凡的婚姻。
命运波澜不惊,她要自己书写。
而一段属于郑念的美丽传奇,才刚刚开始。

结婚后,战事频繁,
郑念随任外交官的丈夫一直在外漂泊。
她的女儿,就出生在澳大利亚。
1949年,反其道而行,
郑念毅然随夫主动回到上海——
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郑康祺曾受聘为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,
后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。
壳牌石油是1949年后唯一特批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,在当时石油产业基础薄弱的大陆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1957年,丈夫患癌症去世,
郑念接着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。
那时的上海不能说一片狼藉,
但也可谓百废待兴。
只从服装上就可见一斑:
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了风靡一时的“时尚”
无论男女老少。
这跟穷有关,但也是那时的时尚。
一些有钱的人,为了不与大众趣味脱离,
也只能跟风穿。
但郑念,似乎没有这种觉悟,
她试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——
只穿旗袍,家里陈设明清古董,出门有车接送。
她在上海的家,被一位老朋友称作是“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。”
连郑念自己也对自己家充满自豪感:
“我的居所,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,
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,
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。”
郑念并不自知,这种努力本身,
是对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,
在不久的将来,这种抵抗,
将让她接受命运的蹂躏。

1957年,丈夫去世后,
郑念不得不独自一人照顾女儿。
那年她42岁。
历史的大潮已几起几落,
失去了丈夫这个依靠,郑念却依旧孑然从容,
有意无意与浮躁的社会疏离着。
她家有丰富的唱片收藏和唱片机。
平常工作之余,就和女儿梅平躲在家中听唱片,
也乐于邀请女儿的朋友来家中一起欣赏。
但平静的日子,总是很短暂。
终于在1966年一个闷热的清晨,
郑念被裹挟着进入了这场历史风波的中心。
只是,在预感到风暴临近之时,
郑念并未慌乱。
先是早上,面对两位不速之客,
“我故意把步子放得悠闲缓慢,
极力做出镇静自若的神态。”
中午,郑念被迫参加了一场批斗会。
晚上,家里的佣人很为她担心:
“你这样孤零零一个人,我们真不放心你。
假若先生还在世,那就好了。”
“谢谢你,陈妈。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
告诉老赵和厨师,不要为我担心。”
嘴上说不担心,但她确实想念丈夫了。
“自他逝世后,我这还是第一次,
不为他的去世惋惜。
谢天谢地,他不在了。
否则,他必然难逃一场凌辱和迫害。”
她想起了亡夫,却不是哀怨命运,
反是为丈夫庆幸。
她51岁了,毕竟还是一个女人,
可在面对可能随时把自己碾得粉碎的风暴面前,
优雅从容,紧张但不畏惧——
命运或许如刀,那就让我来领教。

不可避免地,1967年,
郑念还是被投进了看守所。
理由是她资产阶级式的生活,
长期留学供职国外,有很大的间谍嫌疑。
郑念当然不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,
因而在没有任何审判的情况下,
在看守所饱受6年多折磨。
看守人员惊奇地发现,
这个依靠剥削压迫佣人,
过着腐朽资产阶级生活的老太婆,
依旧把狱中生活过成了“资产阶级”味道。
她借来扫帚,把监牢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还给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尘,
甚至还编了一套运动操,让自己保持清醒。
每当看守员嘟囔着嫌麻烦时,
她就振振有词地背出语录:
“以讲卫生为光荣,不讲卫生为可耻。”
让看守员无言以对。
就这样,她把狼狈不堪的狱中生活,
过成了其他囚犯羡慕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当然,并不是只有“诗和远方”,
有段时间,她的手被长时间反铐在背后,
但即使拼着手部致残的后遗症,
她也坚持每次上完厕所都拉上西裤的拉链,
只因为敞开裤链“太失体面了”。
她也从未放声嚎哭,向看守祈求,
因为她受到的教育中那是“不文明的”。
6年间,她从未承认任何罪名,
也从未揭发任何人。
那时,在交代材料的底部,
落款照例是“犯罪分子”,
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“犯罪分子”前面加上“没有犯过任何罪的”这几个字。
命运要判她有罪,可郑念坚信,命运可以改写。

终于,1973年,有人向她宣布,
将要对她宽大处理,释放出狱。
未料,她竟然拒绝了释放,
反是强硬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,
并且要求赔礼道歉,
还要在上海、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。
“疯了。”他人眼中,郑念的要求很好笑。
最终,两个人强行架着把她扔到了街上。
此时,站在大街上的,
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,
体重从100斤,降到70斤。
回到住处后,
时隔多年,第一次照镜子,
看到自己的衰老、憔悴模样,
她大吃一惊,
“只有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明亮,
这是因为我随时要提防外界。”
这双明亮的眼睛,只是在听闻唯一的女儿死了后,
稍微黯淡了一瞬,随之重焕光彩。
她不相信女儿像她那么热爱生活,怎么会自杀。
她没有因为失去了唯一的女儿而消沉,
反是积极治病,重新修缮住所,
并动用一切关系追查女儿死亡的真相。
她老了,虚弱了,可依然斗志昂扬,
生活只要还在继续,她依然要活得漂亮。
不是证明给别人看,
更是骄傲地活给自己的命运看。
1980年,郑念去了加拿大,
随后定居在华盛顿。
她的离去,不是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,
而是胜利者的姿态——
她的罪名已全部被平反,
在她的顽强追索下,
迫害女儿致死的凶手也已经伏法。

命运待她从来不公——
因莫须有的罪名,入狱6年,
唯一的女儿在此期间去世。
时间于她异常残酷——
生命的下半场,孤悬海外,
独自抵御岁月的侵蚀。
踏上离开祖国的船时,她已经65岁了。
命运从来不曾放过她,可她从来没有推,
留下一身的伤痕和内心的疲惫;
她也从来没有放过命运,那些走远的望和念,
她依旧准备拼命去追。
1987年,她出版了全英文写作的《上海生死劫》,对那段不堪岁月进行了深刻地回忆。
一经推出,就成为风靡欧美的畅销书,并一版再版。
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都忍不住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写书评:
“在人的水平上,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,
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。”
也正是在这本书中,她用了笔名:郑念。
既是纪念丈夫,也是纪念女儿。
而与其说,这是一部回忆录,
毋宁说,这是她改写自己命运的记录——
记录下一个真正高贵美丽的灵魂,
记录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。

与张爱玲在美国的孤凄晚景相比,
郑念的晚年要优渥充实得多。
她在华盛顿高档住宅区购有二房二厅四个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。
她的生活依旧优渥,但不奢侈。
她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“梅平基金会”,
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。
只是生活中的她,要独自体味孤独。
“在美国,一个老年人,没有家、没有孩子、没有亲人,是很苦很苦的。”
晚年接受采访时,郑念这样说。
2009年的一天,她在浴缸里摔倒起不来,
因一人独住,无人知晓。
好在次日上午,她约好的一个朋友来访,
按铃无人答应,特地叫来大厦管理员打开房门,
郑念才被送入医院,但已元气大伤,
医生告知她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年。
她听了,平静地回答:
“我已经活够了,我要准备回家了!”
数月后,郑念走完了她的一生,
以94岁高龄辞世。
回头再看她去世前的影像,
从她的眼中,似乎一点看不到岁月孤苦的痕迹。
《上海生死劫》中文译者程乃珊感叹:
“她是那样漂亮,特别那双眼睛,
虽历经风侵霜蚀,
目光仍明亮敏锐,只是眼袋很沉幽,
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!”
时光虽然磨蚀了她的容颜,
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她身上高贵的气质,
那种透过岁月尘土夺目的美,摄人心魄。

在郑念逝世后,人们纷纷赞其为“最后一个贵族”“最后一个名媛”。
她,当得起这样的称赞。
但,贵族和名媛的评价,未必更准确。
也许,“真正的美人”,才是对郑念最高的评价——
无论身处何种命运的漩涡,
她都不放弃去发现人生的美,创造生活的美;
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,
她都只听从内心对尊严的坚守,要美得体面。
这,才是对一个女人最高的评价:
真正的美人,她们其实是具有更高人生质量的人,
从未让年龄捆绑她们的人生,
都以极大的勇气相信可以改写命运,
进而抵御命运的无常,
就像从没有不需要抵抗重力的飞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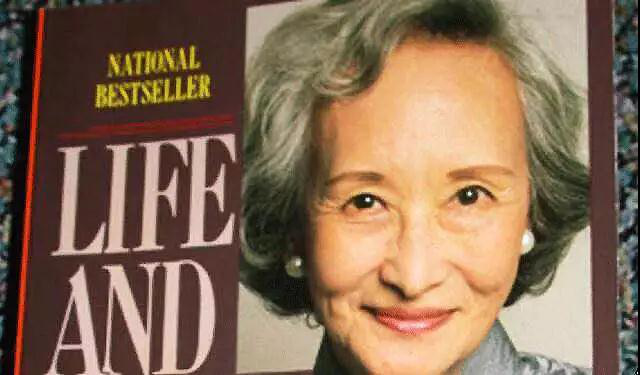
人过40,命运如刀,一直摧残着郑念的容颜,
反倒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郑念,
不断释放出人生更大的能量。
那么正值黄金年龄的我们,
是否更意味着无限可能?
扬在脸上的自信,长进心里的善良,
融入血液的骨气,刻在生命里的坚强。
郑念用其一生诠释了何为坚强
——命运或许如刀,亦要从容应对。
生命如歌,总有高潮低潮,总有顺境逆境,
有时需要浅吟浅唱,有时需要引吭高歌,
而最重要的是从不放弃自己。
坚持着,让生命成歌!
这样的特质何尝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?
城市里的夜晚,
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,
也许欢乐着,也许哭泣着,
也许骄傲着,也许隐忍着,
也许传奇着,也许平凡着,
也许笑着笑着就哭了,
也许哭着哭着就笑了,
但无论是哪一种,
这都是生活,
或许我们应该学会释然和洒脱
但我们更应该学会的是,
坚持自己,执念前行。






